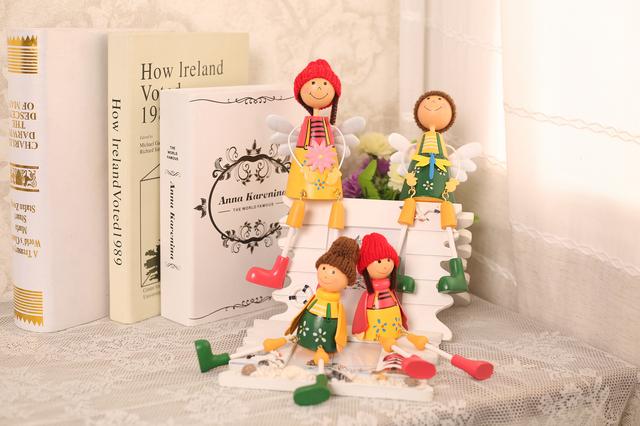车克全,好写散文,文若其人。率性而为,兴意而作,意想用自身的感悟打动自己的灵魂。作品散见于各级文学报刊。
曾记得,沿着山里人踩出的这条蜿蜒而逼仄的山路往下,来到山脚,而后踩着露出水面的垫脚石过了河,上了岸,走上街,这时炊烟点燃青砖黛瓦,氤氲村头招手示意的老槐树,柴草烧焦乡村独有的土腥气,扑面而来的幽香,缕缕的,淡淡的,微醺怡然间,你已拽着时光的美好走进了我魂牵梦萦的故里。
已是午后,秋阳依然散发着温情,挽留下的这片褪色的山景,任由秋日的目光全然透视:山色苍茫间土脊暗伤,丛草泛黄中未见牛羊,飞鸟追逐着流云衔走了骨子里守望着的葱绿,柿子黄了竟为无人采摘而颜面羞涩黯然,树下散落的光影错乱在远行人的背影上,随手摘一枚山枣,荆棘扯疼了连心的手,始觉指尖上流下了心酸的殷红……也许,这时根本不需要有语言,然而,只要静听便有喃喃的声音,是谁在清点枯叶的不时坠落,一片,两片……是谁在边笑看落叶之轻,边数落山风的不情……然而,掀开一页山岩,拂去一层尘土,秋风瑟瑟不安的心绪又是为谁摇曳……在山野穿行,于河水浮漫,随炊烟袅袅,秋风演绎着风车般的坚守,但谁又心知,其安身立命之本还在于穿越时空,追根溯源,去寻找和触摸存储在山岩、河流、炊烟里那些乡土人情的况味,以至吹拂开来,历久弥新,回味绵长……
站在山头,手遮阳光,眺望村舍。脚下这片山丘深深地烙下我儿时的印记:鸡鸣晨起,晓光初上,山脉宛如弯眉,东端粗高西端低细,眉间还系一束腰,神气俊秀,势如一副激情开怀的臂膀,缠绵于河流娇柔的搂抱,蓦然醒来,起伏于闲云之下;暮钟归来,余晖回眸,山貌又宛如一个弯状的葫芦,安逸地睡躺在水雾缥缈的河面上。大自然造化,神工天匠泼出的水墨如此独出一派,让人感慨天地间,不知是青山承之厚重,还是秀水载之厚福。
小村坐落于环水面山之地,村民泽被于青山秀水而居之,以山水为尊,且择其山势取其水义,取山名为“葫芦嵦”。老辈相传,葫芦意为“福禄”,那水浮葫芦与我之村落,此乃大有庇佑之意,真可谓天赐宝地啊。我打小有了山的概念,就是萌芽于这种古朴而美丽的传说。
最初爱这座山,缘于这条山路。那时,每逢镇集就可以随从祖父走这条山路翻山抄近道去镇上,赶集回来嘴里总有余味咀嚼,记得最喜欢的收获是祖父为我买的两块磁铁石。自此身边就多了几个小伙伴,我们经常聚在河滩上吸铁砂,然后将铁砂集中撒在铁皮盒盖上,让磁铁石翻滚其中,磁铁石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时便穿上了厚厚的铁砂衣。如是把磁铁石放在铁盖下旋转,盖上的铁砂会顺时随势地转动起来,如是用磁铁石的另一面在盖下转,那铁砂就会出现一柱一柱的立着转的奇妙景像。有种玩法最不可思议,就是将两块吸在一起的磁铁石掰开,而后用其另一面来相对,两相排斥产生出意想不到的对抗力,任凭你怎样对总也对不到一块去。这些魔幻般的现象既神奇又好玩,是陪伴和快活我玩童时代的乐趣。直到后来上了初中学了物理课和自然课,心底久存不解的奥迷才终于解开,也让我懂得了自然规律不可违抗的原理。
到了上小学的年龄,踩着这条山路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故乡。从此以后我总盼着学期放假。假期开始归故里,假期结束回城里,如此往返,可我从不会忘记,来回必定是特意地走走这条山路,不在乎崎岖,不在乎泥泞,不在于路近,而在于站上“葫芦嵦”的山顶,或前瞻或回望,总能饱含热泪,深深地吸足那口沁人心脾又耐人寻味的气息,那是一种渴望,一种留恋……
故土是心中难以割舍的磁盘,山路是连接故里与城里的血脉,它们始终吸附和流淌着我四时如春的记忆与梦想。
走下山来,河水枯瘦如溪,恍惚于裸露出河底的顽石间,枯黄的树叶挨挨蹭蹭,不知趣地顺水游离而去,冥冥中也婉转而远去了我的思绪……
儿时,我喜欢从这里随手撇上一块簿石片,看那透亮的河水泛起一串串调皮的涟漪,见那涟漪下的鹅卵石、小鱼虾、水草颤颤巍巍的悸动。那时,山下这条不宽的河,平日里河水在低洼的河床一侧缓缓地,东来西去,不湍不急,弯曲地流淌着村民闲适而简单的生活;沿河的山岩,偶有溪水从草丛掩隐的间隙投奔河流,淙淙的回声清脆悦耳;还有乡亲们尊为仙水的——“凉水碗”,那是山崖下一处被山泉冲出的碗状洼池,不管天寒地冻,泉水四时不息,宛如葫芦里倒出的一碗玉液琼浆,喝一口清醇甘爽。池面,朝见薄气氤氲,午看日彩荧然,暮映树影婆娑,月透冰清玉洁,此乃仙水之地;到了雨季,山洪水泻,河水滚滚,河面满而不溢,从未有见河水漫堤冲淹村庄;雨后,大水退去,那河的拐弯处,洪水漩涡冲击而成的一潭深水湾,便是大人孩子游耍戏水的好去处,一个猛子扎入水中,霎时水花溅起了一连串的欢快的笑声……
山岩土色灰黑,临近河面处苔藓墨染,柿子树顽强地攀悬在岩崖上,横曳斜出的枝叶倒映在河里,风吹影动,水中的小鱼悠然摇摆着自在……村民守着故土过日子,祖祖辈辈沿袭着抱朴守真的民风,他们醉心于这素有“世外桃源”之誉 的境地,信奉着平安是福,也忙碌在朝夕相处的山水里……姑姑从山上背下沉甸甸的柴草,口袋里藏有鼓鼓的山野果,来到“凉水碗”,缷下柴草,掏出一捧山果,在池子里洗净,在衣襟上蹭干,顺手塞进我巴巴张着的嘴里,见我涩涩咧嘴的苦笑,她却一个接一个地吃着、嚼着,那有滋有味的样子,仿佛咽下得是劳累,咂巴得是收获里的脆甜滋味;爷爷从山后的田间来到河边,蹲下身,先洗去脸上的泥尘,又扯下脖子上的毛巾,透洗去脊背上的汗渍,而后刮洗粘在锄头上淤泥,累累的喜悦堆积出丰收的面庞,就像身边背筐里露出的刚刚摘下的黄柿子,成熟里透着亮;一壮汉肩背土枪,左手提着野兔,右手拎着山鸡,莽撞地走下山来,嘴里的口哨吹出粗野的调子,引发河里的鸭鹅一阵“呱呱”的躁动。
巷子不深,街面不宽,邻里的年轻村姑和小媳妇们像约好的一样,先后来到河边,从水里搬一块条石作搓衣板,衣物在手中搓揉浣洗,碱粉和胰子(肥皂)沫在指缝里发泡,不时冒出男人的烟草,孩子的奶腥,和长辈旧衣浸湿出的孝道的气味,家长里短在泡沫中消解,嘻嘻哈哈地说笑声,砰砰啪啪的棒槌声,此起彼伏,交响出乡里乡邻亲情和美的乐曲,回荡在山水依依快乐的韵律里……那阵子,记得还有人在河的下流淘洗着砂子,稀有的黄金偶尔会给淘金人带来惊喜,也洋溢着村岸上的人们向往着金子般生活的美好梦想……
走上村街,夕阳的余晖洒落街面的寂静,恍然间感到有些陌生,此时应当有晚炊诱人的味道,应当有鹅鸭从河里蹒跚归家的不绝于耳的“嘎嘎”的叫声,可家家关门闭户,巷街路人不见,空气静如凝滞……我纠结于儿时的追忆,一边四周张望,一边向原来的老宅走去。忽然心中一喜,只见一年龄好似相仿的村民迎面走来,“朋友,你找谁?”熟识的胶东乡音,带着暖耳的温度。“我小时候就住那屋!”,我手指老宅和声悦色地答道。他先是一愣,又急忙近前上下仔细地打量我,随后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呵,你是‘洋钱‘……?” ,“你是……‘大虎’(小名),村支书?”,一阵寒暄,“大虎”力邀我到村东新村家里作客,我说明了要去邻乡看姑姑的原意,他不再坚持,拉着我的手,一边聊起玩伴时的趣事,一边陪着我走向老宅。他讲:“你来得正好,这里已列入市里的规划,不久这老宅……”他大概顾忌我的感受,抬头巡视一下村舍,用“嗯……”的一声长音结束了他的话。“我坚持保护老村村貌,凡新盖房屋楼舍,一律移址到村的东头。这些年,年轻的劳力都进城里打工去了,剩在家的老人和孩子,大多住在新村了。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比较突出…….",他继续地讲着,语气里带有些许念旧和担忧,这无意间竟暗合了我的所见所思。
一声“洋钱",久违了。已模糊在记忆里的绰号,立马唤起我伤怀的感慨,这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从“咿呀学语”时起,我就远离城里的父母跟祖父母一起生活。祖父母视我如掌上明珠,加上那时家乡人把城里人看作是“洋人”,花得是“洋钱”,绰号便由之而来。
抚摸着老宅,体味它的老气横秋。斑驳的墙体上,还残留着人民公社第二小队的工分公布栏;山墙一条裂缝,由宽而窄地蔓延而上,撕扯着粘合在心里的泥巴,舔一舔手指上的土腥味,生命的意味在延续中泛起思索的涟漪…..
门面上,“铁老虎”的嘴里叼着的门环,风吹门动,“当当”的叩响声,仿佛告诉我它依然坚守着家主的尊严;房舍看上去矮了,门前台阶低了,抬头望着屋顶,那一楞一楞的小片黑瓦上下握扣着,瓦间两株枯黄的草杆在风里摇摆着,恍惚间,仿佛夕阳下的一对老人——我的祖父母,牵手相扶,弯腰驮背,颤颤巍巍地向我走来……
那时,老宅的院子是碎石头铺的。早上爷爷从山里劳作回来,放下锄头,接过奶奶递上的毛巾和端来的洗脸水,洗罢脸后,用剩下的水抹洗完屋内的大柜、杌子、桌子等家私,之后便拿起扫炕式的笤帚(有别于扫地用的长把笤帚),蹲着清扫屋内和院落的地面,连边角也不遗漏。日久天长,习惯已成自然。上边来的驻村干部总安排在我家厢房里住;过年时各村相互轮流演戏,来的主要演员化妆扮相、吃住以及道具安放也在我家“客屋家”(当地摆供桌和请客的屋子)。全村公认家宅拾掇得干净整洁,其实是褒奖祖父母善于勤劳持家罢了。奶奶裹着小脚,常年步履在锅台庭院,方寸之间见得劳顿。除每天操持一家人三顿饭、喂鸡喂鸭,还要照顾躺在炕上的老婆婆,她出门的时候不是到菜园摘菜,就是提着猪食喂猪,再不就是端着盆子去洗菜或洗衣服……我爱吃奶奶腌制的咸菜和憋的酸菜,一缸咸菜开缸闻着臭吃着香,一坛酸菜开坛嗅着刺鼻吃着通气暖胃,尤其是就着它喝上奶奶特地熬制的酸饭(粥),倍感生活滋润在咸淡调理入味的日子里。
特别盼望过年,不光有奶奶给的压岁钱,还爱缠着奶奶,看她亲手剪贴窗花,在乡邻四舍里奶奶剪窗花的功夫稍有名气,那双粗糙的手,总会把纤细的日子美美地剪贴在木菱格子的窗纸上;看她亲自揉面扯剂,卡出形态各异的“木卡花”;看她巧手雕塑般地制作“圣虫”、“刺猬”、“元宝”、“葫芦”、“枣饽饽”和特意按属相给我制作的小公鸡。奶奶边制作边给我讲着民间传说,概是些“圣虫”压在粮囤子和粮缸里来年就会五谷丰登,“刺猬”是财神,和元宝一起放在窗台上就会招财进宝,“葫芦”是“福禄娃”,挂起来福禄就会自然来…….之类的祈福故事;小公鸡制作得惟妙惟肖,见我高兴,奶奶就会喋喋不休地 唠叨起我的生辰:“你是晚上八点出生的,是吃饱晚饭进窝的鸡,是宝(饱的谐音)鸡唉!”,每每这时,那种溢于言表的美就会悄然挂在奶奶那张清秀的脸上。蒸面食的火候可大有学问,每当这时,奶奶从不让别人来添柴续火,当笼屉盖一开,见那热喷喷的,开口笑的枣饽饽,奶奶的笑声早已升腾在满屋的热气里了,“又是一个好兆头,又是一个好年头……”,奶奶喜出望外地祷告着,顺手把一块温热的黄米糕塞进我的嘴里,吞咽着甜甜的黄米糕,我哪知里面浸透着奶奶祈求日子过得步步高的多少愿望啊……. 年味是奶奶笑的味道!
铁锁把门。趴在门缝往里看,早知宅主换人久矣,可还奢望味蕾能在老宅寻觅到祖父母留存的味道。许久,“大虎”抚慰地触摸着我,方把我拉回现实。回过头来向他莞尔一笑,又几近哀求地说:“拆迁时请你给我留两片旧瓦吧!如有可能烦请现主人帮我带两片到新的楼厦上,因为我知道那瓦片历经风霜雨雪,久冒天寒日晒,已积劳成疾,也渴望进驻高楼大厦里歇息一下腰背啊……”
抬起头来,望着天上一缕浮云,尽量抑制泪水流下。
日落西山,天光沉降,却见东山沸沸扬扬着一片灰白,尘雾在“轰隆隆”的喧嚣里升级,弥漫中难以掩盖”葫芦”屁股上被剜出的大口子正在“流血”…….大型机械与炸药串通一气,喘息着威逼之势,“葫芦”显得很脆弱,哽咽中逐日忍受肉瓤被吞,种粒被掏,“绿肺”被蹂躏之痛……一辆辆满载碎石子的大货车从料石场下来,碾轧着瘦水的河床,疾驰而过,不知又要川流于哪个建筑工地。车尾卷起的柴油燃烧的废气,夹杂着道路飞扬的尘埃,呛鼻刺眼,临近的屋顶一片落白,不见瓦色。
山里的大庙早在那个年代被“狂热”摧毁,废墟的瓦砾中挺立的两棵白果树,像雾霾沐浴下的两个灰头垢面的证人,正向山神述说着过往的不幸和眼下的无奈…….
我从“大虎”那里得知,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料石场,“葫芦嵦”的确给村民带来了福气。可我在想,富裕当下的歌声正在麻痹中沉醉,有谁还醒在后生的福禄里?不妨你细听,那“葫芦”里正微弱地发出生命的疾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视线在黄昏的眸子里模糊,酸楚的泪花飘洒着割舍不下的温度,被风送回渐行渐远的山水村宅……
与“大虎”的握别几次三番,直到站在村北口大道的公交站牌下,两人才默然相对,良久,“大虎”终于开口:“唉,对了,光顾得陪你走着叙旧了,还忘告诉你,市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规划已分步实施,你姑姑那乡试点得早,现已见雏形。我村依托尚有的山水脉络的独特风光,已纳入新型旅游城镇建设的定位,料石场年底停产,保证不出三年,你再回故乡,那将是另一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新景象了。《规划》可见,‘葫芦嵦’的山林果树花草养护有了考核新规;从传承文化着眼,原址原样重建山庙和戏台有了图纸;拦水库坝正在兴修,村前河水将四季长流,河面冬季可滑冰,其他三季供漂流;旧村农家四合院或修旧复旧或依样翻新重建,力求保持原始风貌;街巷亮化和拓展商业、餐饮诸功能正在运作资金,打造吃住行游为一体的,各项设施完备配套的,以旅游经济为主的新型城镇的整体方案已在论证中出炉…….”。“大虎”兴奋着我的兴奋,让我仿佛沐浴着春风,看那些含苞欲放的美丽花蕾正铺设着新农村前行的大道……
一辆公交车戛然而止。上车前,我再次回望了“葫芦嵦”一眼,忽然感到,积压在心底里的那口奶奶塞进去的黄米糕的滋味终于泛了上来…...
主 任
戴升尧
副主任
阿占 林之 张金凤 张祚臣 盛文强
委 员
高伟(兼)刘宜庆(兼)张彤(兼)王小姿
王俊 孙邦珍 米荆玉 阿丫
如风 李蕾 安东 肖瑶
雨桦 崔燕 崔启昌
崔楚平
主办:青岛市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
主编:张祚臣
编辑:孙邦珍
LOGO设计:阿占
图片:选自网络
投稿邮箱:77914171@qq.com
欢迎扫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