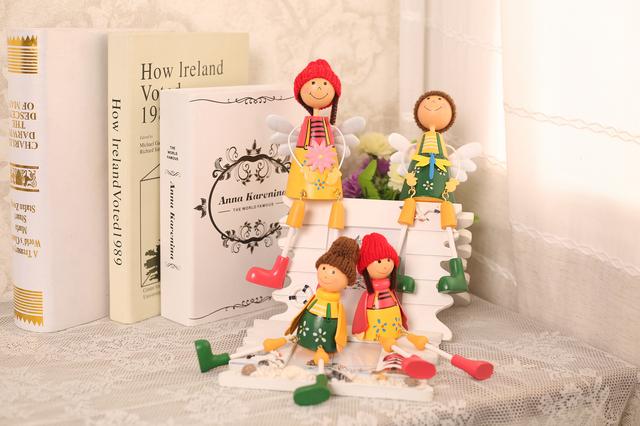写他们之五
黑白的素描
我有一支木笔。
它用洋江西湾旁那颗古槐的劲枝修磨而成,高至肚脐,粗如铁锹木柄。清晨,在那棵古槐下,我迎着朝霞,提着木笔,看见一个个熟悉的农人沿湾走去,留下高低不齐的背影,他们把村落叫醒了,让村落活得有模有样。我将木笔蘸满湾水,水滴淌在地上。我顺着那些远去的背影,葫芦画瓢,在地上描摹着他们的行动和说笑,泥土上的图案便渐渐清晰为人迹。我像一位书画家那样作势挥笔,这一个个图案又定格成了某一处无言的片段。
我伏在古槐上,静静看着图案,等着他们返回、路过、笑说。
但他们再也没回来。
于我眼中,这些素描便活了。
一攸光景:晨夜眠人
我用木笔在地上画一根蜡烛,然后用沙土将它盖住,像夜色吞噬了稚弱的火苗,演绎出一片冬晨的灰景。我循着曾无比熟悉的路迹,一撇又一捺地画出了八爷家的屋门。
我在门外高喊一声,喷出了清晨第一缕雪白的雾霜。老屋也咳嗽一声,传出一阵窸窸窣窣。八奶用细长的公鸭桑说使劲推门,右扇门没插——“嘭”一声,迎面扑来一股腐烂味道,和着淡淡的尿骚气。
这是洋江独有的口气,粘稠而均匀。
八爷翻身卧起,“嗤啦”一声点燃灶台的煤油灯,映亮了龙钟皱脸,白须围成的嘴唇像一个脏兮兮地鸟窝,含着一条白虫一般,顺着豆大光丁吃起了旱烟。八爷肺痨比驼十爷厉害,每天早自习我过来喊八爷的孙子艳波结伴上学,他总会准时醒来,或许早已醒来,无视了站在屋中的我,无视了八奶对艳波懒惰的遍遍呵斥,兀自一人呆卧吸烟,不停地咳喘,一屋子烟气,一屋子黏稠。我静静等着,看那一家子老小挤在炕上黑乎乎的如屉上地瓜,却总被那一缕光线吸引过去,像是触摸着一段油黄的历史,那个说书人,正是八爷。微弱的火花模糊了曾经历史的内容,只有他斑驳不清的脸庞,分不出喜忧,一口接着一口,一根接着一根,烟气从他蜷缩的被窝中袅袅袭来,静寂悠长,不动声响,怕惊扰了尚未苏醒的夜么?
炕上一阵蠕动,几个尚未成婚的儿子被光与烟扰醒,懒懒地翻身打个呵欠,再挤在一起,像地瓜翻身。艳波终于下炕背起了书包,我简单地和八奶告别,门“吱呀”一声闭了,外面好凉啊!
走远了,我回头看,几丝暗光从窗中透出来,浅浅照在地上。我才忆起,我没有和八爷告别,一次一次,从来未有。
公鸡未叫,正是好觉!
我终究不知道羸弱的八爷,都在想些什么。他或许在等待,等待煤油灯燃尽的那一刻,他才能安心得睡个囫囵觉,任凭村北盐碱地里的北风呼啸而过,孤狼野兔追逐而过,他自眠得安然自在。
一抹斜阳:牛困人乏
我用木笔浅浅画出一个人的脚印,再画出一个牛的蹄印,左右成型,因为盛夏的洋江,人牛无异。
所以,那个叫勺子头的男人便那么自然地在我笔下出现了。我画出一个低头走路无言的他,再画出一只疲沓沓的倦牛,让他们相遇在斜阳的红霞里,平凡且卑微,日复一日,重复着下地还田的光景,如日出日落准时而执拗。
他仿佛与生俱来的本分和使命就是下地干活,我看见他牵着牛车,车上坐着雕塑一般的老婆,低着头、缩着背,两只脚一前一后均匀迈着步点,不发一言,不多一眼,过来了,路过我的童年,又走远了。他身后的牛,他路过的鸡鸭鹅群,甚至是脚下踩扁的小草,和他一样成为干枯洋江没有滋味没有色彩的装饰。
我从没见他在酒足饭饱里开怀大笑,也从没见他于熙攘人群里高谈阔论。或许,骄阳鞭策下,冒着热气的泥土地里才偷偷绽放着他的理想;星光夜话中,四处奔走的夜风里撩拨着他肆无忌惮的思绪。只有在这些时候,他才不是人们眼中的勺子头,才不是那个令生活空乏到虚脱、成为洋江一代代沉默农人符号的勺子头。但在我的记忆里,他始终未挣脱斜阳下的那一路无言的束缚。他的前面,他的身后,无数农人和他一样,和驼十爷一样,和狗蛋大爷一样,路过我的童年,走远了,就像冬天来临的时候,我站在瑟瑟寒风里,在冰凉的黄晕里,他们忽然消失无影,但这并非一个点赞的冬季。因为泥土地已经冬眠,它们此刻没必要、也不需要勺子头们日出而作,再给他们春华秋实的褒奖。我看见勺子头在雪地里拾草、喂牛、坐卧,依旧沉默无言,对生命无欲无求。
我将木笔蘸满水,水又一滴滴淌下来,落在他的画像上,像一粒粒饱满结实的汗珠儿。
一门生计:火光铁影
夏日的空旷与浮躁,往往来得令人猝不及防。加上蝉鸣的聒噪,疲倦的树叶和蔫吧的禽畜便更加无趣,谁来装饰这枯燥的世界?
相比我手中木笔,我更相信一只铁笔的力量,经过火光的淬炼,在古槐树下描摹得风生水起。
若问铁器何处有,顽童遥指洋江村!
两个铁匠一胖一瘦,正在村中心的十字路口处忙活。他们一年一趟逐村转,我的印象中,蝉来了,他们也就来了。胖的负责风箱烧火、小锤敲尖和做饭,瘦的负责火中淬铁、大锤去屑和凉水定型。两人搭配默契、手法熟练,将一块块生了锈的铁刀、铁锨、镰刀、锄头放进炭火中猛烈灼烧,通红变软后,夹出来放在铁砧上,瘦的抡着大锤高低抑扬,胖的舞着小锤细腻铿锵,“铛铛”脆响宛若音符。在小锤一阵眼花缭乱地“砰砰”打磨后,一个原先脏兮兮、锈斑斑的器具变得瓦明正亮、锋利无比,明晃晃地反衬着骄阳,令人啧叹。
斜阳晚烟,人群散尽,疲累召唤着生计。胖铁匠在水桶里涮涮手,在炭火上架起铁锅,干脆利落地赶出些面条或面疙瘩,炝锅煮水下面,一袋烟的功夫,两人已经热乎乎地吃上了面,像一对匆忙而充实夫妻。掌灯了,两人又收拾着沉甸甸的夜色钻进支起的帐篷,就在炭火旁和衣而睡。月光星花,荷塘蛙鸣,都成了帐篷的陪衬,诗意和远方从未如此唾手可得。
他们的存在渐渐成为村人习惯的时候,忽一日清早,阳光不再灼热,大地静寂得厉害,那十字路口上,竟不见了他们搭档的身影,我的心里就少了一样东西,空落落地不知所措。我自不知道他们何时动身离去,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方。但那个路口上,留下了一团黑乎乎的碳渣,就像一团蝉的碎片。原来蝉鸣也息了。没了蝉鸣的季节原来比蝉鸣时候更无趣罢!而我手中描摹他们的木笔,始终不能清楚名状他们的行走坐卧,他们的名字姓氏,家乡故籍。唯有画一只蝉,垒一堆碳屑,祭奠他们生命的神形。
因为一只木笔,终究比不了火光淬炼出的铁笔。
一片坦途:无光精灵
纯澈的黑色,对我来说是一种诱惑,譬如那安静到窒息的洋江夜晚,能馈赠于灵魂无冕闲适。
对另一些人,黑色是生命本质,譬如这个叫做“瞎丫”的老头。
大人说,他是天生盲,一落地就是黑色。黑色给了他黑色的眼睛,却没有禁锢起他对生命的追逐。我的童年因此漫步着这样一个卖零食的老头:穿一身破烂单衣,挎一筐子,柱一木棍,揣一铜锣,边敲敲打打,边扬声念道:“拿酒瓶子来换瓜子花生哟——拿酒瓶子来换瓜子花生哟”,碎步由远及近,锣声清脆馋人。只要锣声响起,孩子们的魂便没了,全被瞎丫敲进了那盛满花花绿绿糖果的破筐里。
大人们看着瞎丫从容不迫把孩子们递上来的酒瓶、纸币、银元算得分毫不差、摸得真真假假,再等价交易出瓜子、花生、果冻、糖豆;见他闻声就能分辨出双喜、艳情、涛涛们,带着戏谑口吻称赞道:瞎丫精啊,一个瞎子围着好几个村子转来转去,哪里拐弯,哪里有沟,哪里是猪圈,哪里是土堆,都能被他轻描淡写地绕过去,他是怎样从一个黑无尽头的世界厘清这常人都觉得混沌的世界呢?有人怀疑他是否真瞎,在他面前摆手做鬼脸,甚至吓唬他恐吓他,他依旧面无表情纹丝不动,看不出对世界任何的抱怨和献谗,唯有双手把装酒瓶子的布袋口扭紧,把盛果糖的筐子把严。他掐算着时辰,该走了,柱起木棍敲打着离开,绝不拖泥带水,从未犹豫不前。对大多数盲人,能藏在家中自理已属不易,谁能料定他竟然能在黑暗中如履平川,靠一个不起眼的小买卖营生,每日独自摸索数十里,来完成生命的自我救赎?他肉体残疾,却没人敢小瞧他,没人会嘲讽他,因为世间欠他太多,他却从不负人。
他一生之谜如他眼疾一样永无解药,我便对他眼中的黑色充满了敬畏。当他一路远去的时候,“哒哒”敲地的木棍在地上画出纹路,远璀璨于我在古槐下的描摹。他能用木棍回应着光明世界,我们呢,如何走进他黑暗精灵的旅途?
我的怜悯,此刻便显得如此多余。
我的木笔渐渐被磨短磨平,伤逝在地上成素描的痕迹,我便准备将它扔掉。它从古槐而来,夕阳中,我又将它放回原处,竟不差毫厘地填满了树枝的沟壑。夕阳落下,夜幕袭来,古槐晃动着枝叶,反衬着斑驳的月光“沙沙”不止。
我伏在古槐上,将耳朵贴紧树干,听那经久不息的“沙沙”声:沙沙、沙沙、沙沙,那是清晨远去的农人陆续返回,经过西湾,正与我痴迷的浓夜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