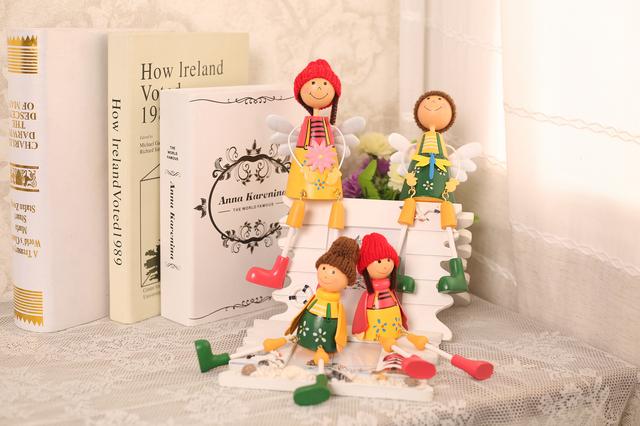(一)
正午火辣辣的太阳,穿透瓜棚薄薄的茅草顶子,把热浪一丝不减地送进来,我被这团热浪包裹着,一边抹着脑门子上的汗,一边翻一本没有头尾的破书。书是从老蔚的床底下翻出来的,头尾都被撕掉了,估计是拿去生火了。起初我很兴奋,翻开之后却大失所望,这是一本讲春季病虫害防治的书。我聊有胜无地翻着,读到生石灰水如何涂上树干防虫时,终于忍无可忍,把它丢在一边。
没有风,四周静悄悄的,也没有声音,世界仿佛静止了似的,只剩下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这是一天之中最热的时间,大人们回家做饭了,留下我和大黄在瓜园子里看瓜,大黄和我一样无聊,趴在我脚下,四仰八叉地耷拉着眼睛,它的窝原本搭在外面平台上,却被太阳一点一点赶进来。
瓜田在一片洼地里,三面都是崖畔,南面是一条水渠,瓜棚就搭在东面的崖畔上,所有胖西瓜都在我的脚下一览无遗,它们一天到晚都在呼呼大睡,太阳越晒睡得越香。除了欣赏欣赏它们胖嘟嘟的模样,我很少吃它们,老蔚在瓜园的角落里种了十几株西红柿,一大片凤仙花,那里才是这个瓜园最吸引我的地方,饿了就去摘西红柿,太阳落山后就用凤仙花叶包了花朵染指甲,一个假期我的指甲上都是红红的蔻丹。
知了在树丛里“热啊……热啊”地叫,刺目的太阳光照在平坦的庄稼地里,让人无处可藏,瓜棚是最大的一块阴凉。我又折回去,坐在椅子上,大黄也起来了,哼哼唧唧用耳朵蹭我的腿,我拿起一块西瓜喂它,它不肯吃,扭转身子,尾巴卷成一个倒写的6,在我眼前晃,我百无聊赖地卷它的尾巴,想卷成一个8的形状,他吃了痛,“吱”地一声跳开了,反倒吓了我一跳。
“姐……姐……”卡拉在叫我。
我跑出去,卡拉正站在水渠的对面,看见我一个大步跨过来。他是三爸家的小子,我们俩在村里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我叫安娜,他叫卡拉,都是迷恋苏联小说的小爸给取的,不像伙伴们都叫什么向荣、卫红、春妮。
卡拉一过来,大黄就做出一副防卫的姿势,但他却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肉包子,大黄闻到了肉香,摇头晃脑地大嚼起来,他就势搂住大黄,掰它的眼皮,揪它的耳朵,骑它,拽它的尾巴,大黄被他搞得烦不胜烦,一咽下包子就翻了脸,龇牙咧嘴,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吼叫。他又拿起桌上的西瓜讨好大黄,大黄轻蔑地瞅了一眼,转过身去,他没辙了,趴在老蔚皱巴巴的床上一声声地唤:“大黄……大黄……”他穿着白背心,蓝裤子,晒得黑溜溜的,像一条小黑泥鳅。
叫着叫着眼睛一亮,“姐,要不要知了?”
“知了?要。”
他一溜烟就跑出去了,几分钟以后回来了,扣着两只手。
“要哪一只?会叫的还是不叫的?”
知了扑腾着翅膀在他手里挣扎,乌黑圆鼓鼓的身体,突兀的大黑眼睛,我突然发怵了,缩回手不敢碰。
“别怕,这又不咬人!”可我还是不敢伸手。
卡拉把一只知了扔在地上,大黄一下子扑过去叼走了,他腾出一只手,翻出一截线头绑在知了的前腿上,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提着,还没来得及仔细看,知了突然间横飞直撞,翅膀“啪啪”地打在我的脸上,我吓了一跳,手一松,它带着线头飞走了。
“咳!你胆子真小!”卡拉在一旁跺脚。
大黄吃了一只知了,巴巴地看着卡拉。
“那边小树林里还有好多,咱俩去抓了喂大黄吧。”
我把大黄拴在木杆上,卡拉在床下翻出一个脏兮兮的洗衣粉袋,递给我。
太阳渐渐向西斜了,像妈妈的眼睛一样侧望着大地,一天之中最难熬的时间过去了,我的身体也变得轻快起来。水渠里的水有一点点混,悠悠地从我的腿间流过,我站在水里洗那只洗衣粉袋,袋子渐渐露出粉粉的颜色,上面画着一只娇艳的山丹丹花,旁边写着几个大字“山丹丹洗衣粉”,上学之前我已经认得这几个字了。
水渠南岸有一小片杨树林,都是刚栽下不久的树苗,枝条柔软得像小孩的腰肢,上面落了好多知了,“知呀……知呀……”地叫仿佛一个小合唱团。我撑着袋子,卡拉轻手轻脚走过去,弯下树枝,一抓一个准。庄稼地里的知了真笨,即使惊动了它,它也只会飞到一个看得见又够得着的地方,不像村子里的知了,狡猾的很,一点点风吹草动它都飞得又高又远。袋子满了,可是卡拉正抓得高兴,把剩下的知了装进裤兜,知了在卡拉的裤兜里昏头懵脑地向外爬,我跟着卡拉,一手提着袋子,一手帮他摁着裤兜口。
回到瓜棚时,老蔚已经弓着背在地里翻西瓜了,她穿着一件碎花短袖一肩高一肩低地支着腿,花白的自来卷头发乱蓬蓬地交织着,一双粗大的手衬得墨绿色的小西瓜娇嫩无比。这些西瓜是老蔚的孩子,她珍视它们,抚摸它们,把汗水滴在它们身上,满怀希翼地看着它们长大。西瓜是个贪睡的宝宝,要时常帮它们翻身,否则就会长成个阴阳脸,不那么招人喜欢了。
看见这么多知了,老蔚的细眼睛瞪圆了,眼角的沟壑抻成一条条白色的细纹。
“咦!哪里抓的,介个肉可以吃哩。”
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几年,她仍然带着浓重的甘肃口音,卡拉在一旁极力怂恿她做了吃,她嘿嘿笑了,露出稀松的牙齿,搓了搓手上的黄泥,就去扒拢柴火了。
我喜欢老蔚的甘肃口音,这让她显得和周围的人不一样,仿佛是一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不过她的确有好多种庄稼的门道,比如在瓜园里种上大片的凤仙花驱雾;在开花时提一提瓜藤,“后头咔叭,前头结瓜。”这些都是本地人想不到的,更重要的是,她是个有意思的人,会做油炸糕、面老鼠;会在正月十五用竹条扎一个大大的天灯,盘上清油做的捻子,忽忽悠悠地放上天;当然,她也会和我们一起吃知了,我妈和婶婶是决计不会的。
瓜棚后面搭着简易炉灶,上面架着一只小黑铁锅,老蔚把知了倒进铁锅,盖上锅盖,就让卡拉烧火,我惊异地看着他们,原来以为要洗剥干净倒了油去炒,没想到是这么粗笨的做法,知了在锅里扑腾,渐渐地没了动静,这只小黑铁锅是我妈拿来让老蔚烧开水的,要是被她知道烧了知了,一定会把锅底洗穿的。
老蔚是甘肃人,四十年代逃荒来到这里,听大人说,当时她穿着一件破夹袄,挎着个小包袱,冻得颤颤巍巍,大骨架单眼皮细眼睛,说不上好看倒也不难看,被穷得叮当响的胤山收留当老婆。胤山会唱戏,干活的间隙常常背靠大树吸一锅烟唱上一段,早年胤山的爹就是个秦腔老戏骨,一出《金沙滩》《祭灯》唱得男人们都会一声长叹红了眼圈,听大人说,他临死之前让胤山称了一斤锅盔咔嚓下肚,然后亮开嗓子一口气唱满了七十二个再不能,闭上眼睛就去了。
再不能习武科场走,
再不能得中占鳌头
再不能当殿拿本奏
再不能醉打奸臣揭贼短羞,
再不能兵扎军阵口,
再不能设谋把敌诱
……
老牛力尽刀尖死,
汉马功劳旦夕丢
刀斧手押爷上杀场,
大丈夫呀……一死又何妨。
这是秦腔《斩李广》中的大唱段,那一刻唱出来必定倍加苍凉悲壮。胤山继承了他爹对唱戏的挚爱,也继承了他爹一样的不会过日子,老蔚嫁给胤山,对这里肥沃的水浇地爱不释手,很快就成了一个女流之辈的庄稼把式,村里人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甘肃人能吃苦。同时又得出另一个结论:甘肃人邋遢。老蔚能把庄稼打理得青翠可人,却不太会打理自己和家。
炉灶上空飘起薄薄的烟雾,柴草遇到火,烧得噼啪作响,一刻钟后老蔚把火从灶膛里撤出来,掀开锅盖,一种特别的味道飘散开来,有一点点糊味,又有一点点焦香,卡拉和大黄颠颠地跑过去,脸上挂着同样的表情。
知了的头尾都归了了大黄,老蔚教卡拉拨开壳吃中间的肉,还找出一点盐佐那指头肚大的一块肉。他们夸张地砸巴着嘴想吸引我过去,我远远站着,没有胆子看那锅里一眼,直到卡拉剥好一块,拿过来缠着让我尝,我才放大胆子嚼了嚼,很筋道,有淡淡的烟火味,有点像熏肉的味道。大黄欢快地跳着,跑来跑去吃地上的蝉尾,在我眼里,那场面不亚于尸横遍地。
黄昏在不经意间就来了,潮湿的地气徐徐升起,瓜蔓又重新温润起来,小西瓜温温热热的,挂着淡淡的绒毛,像小弟弟光光的脑袋,老蔚在给瓜秧培土,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赭色的皱纹流进鬓角。我爸妈回来了,着人捎话让我回家。
玉米长得有半人高了,我不敢走小路,顺着渠岸向前走。渠岸边大多种的是豆角、棉花、红薯,借着渠水长得枝繁叶茂,雄赳赳已经有了丰收的兆头,渠边上的几棵老柳,大大咧咧地把枝条垂到水面上,我扯下几根边走边甩出呼呼的风声。蓦地,从我身后窜出两只细狗,悄无声息地耷拉着血红的舌头,我吓得一哆嗦,回过头,狗连长伋着鞋远远走在后面。这是他的狗。他家里常年都养着狗,就连粮食紧张人都吃不饱的时期,他也会把口粮分一份给狗,和狗一起饿得瘦骨伶仃,因此得了这么个浑名,他养的狗精廋凶悍,让人望而生寒,不像大黄那么敦厚。
我紧走两步拐过一个弯,远远地看到了村口,水渠边的人多起来了,我也不怕了,有人在洗衣服,也有收工回来坐在石板上洗脚、洗锄头的,天快黑了,上游没有小孩耍水,水流得清澈舒缓。
有两只细狗在前面开路,狗连长把两只水壶交叉着背在胸前,提着一只死兔子走得雄纠纠气昂昂,胖妈被那两只细狗吓了一跳,张嘴就骂:
“你个死家伙,快唤住你的狗。”
“不好好务弄庄稼,领着狗满场跑,都划成自留地了哪有什么猎物。”
狗连长讪笑着扬了扬手里的野兔,“给我老婆下奶。”
“不好好干活,小心你老婆被你气得没了奶。”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狗连长也不分辩,嘿嘿笑着坐下来洗脚,再把脚湿漉漉地穿进鞋子里,洗完之后吆喝着狗走了,我远远跟在后面,数那只兔子身上隔三差五滴下来的血滴。
晚上睡觉时,听见爸爸对妈妈说:“以后别让安娜去瓜园了,女孩家家的,都晒成黑碳头了。”
“那我中午去换老蔚姨,你们吃饭就得晚点。”
瓜田是爸爸单位的闲置地,租给本单位职工租金非常便宜,我们家没劳力,老蔚家缺地,所以就两家合作,主要是老蔚管,妈妈有空了就去地里干活。
明天我还想给大黄抓知了,刚要反对,嘴巴张了一半就睡着了。
(二)
睡醒的时候都已经半晌,妈妈下地回来了,正在厨房里做饭,风箱有节奏地发出一声声唤。我们这里一日三晌,早晨一睁开眼就下地,干到日头高升(9点半左右)回家做饭,饭后再去地里,干到正午(12点多)回家,睡了午觉吃了午饭,太阳不那么毒辣了,才会下地一直忙到天黑,晚饭叫喝汤。很多年以后,我仍然认为这是人体与大自然最为和谐的作息表。
刚吃过饭,表姑就慌慌张张跑进来,禾子哥又和媳妇又打起来了,找我妈快去劝架,我妈解了围裙,擦了把脸就向外走,我颠颠地跟上去看个究竟。
场面并不似我想象的那般火爆,也许是冲突刚刚停止,禾子哥躺在床上睡大觉,嫂子进进出出把门摔得砰砰响。嫂子的嘴唇破了,嘴角抹出一道长长的血迹,看见我妈,一边哭啼啼地说,一边就着房檐下的一只水盆洗血迹,那盆水看起来并不干净,她却一下一下撩到唇边,我想她一定是气糊涂了,忘了那是一盆脏水,我抻着妈妈的衣角,几次忍不住想提醒她。
让人迷惑不解的是,第二天,嫂子又笑靥如花地跟在禾子哥身后去县里了,可见,两口子打架也像我们小孩一样,一时三刻就又合好了。
村子里树荫浓密,呆着固然不热,可是却很无聊,能发掘的地方都玩遍了,只能竖起耳朵等换米糕的、换塑料小玩意的人在街面上吆喝。
天在等待中渐渐黑了,大人们喝了汤,摇着扇子踱到村口拉家常,我也拉着草垫飞快地跑去占了个好地方。
月亮真亮啊,高高地挂在天上,安详地吐洒着它的清辉,在老槐树下投了一地斑驳的影子,这棵槐树很老了,从爸爸小的时候它就长在哪里,树冠像一把巨伞,树根从地底突起虬结在地面以上,然而树身却很诡异地裂开了,露出空空的肚膛,我曾经编过一个故事吓伙伴们:雷电交加的夜晚,四周一片漆黑,老槐树的树干突然间炸裂,从里面飞出一条大龙,张牙舞爪飞上高空……伙伴们深信不疑,但同时我也被自己的故事吓着了,天黑路过这里,总是害怕有一条龙飞出来把我抓走。
女人们凑在一起拉家常,也有人借着月光纳鞋底,男人们坐在凸起的树根上一明一灭地抽烟,锦程光着膀子披着外衣走过来,,把话题从收成扯到十大元帅、、,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是唯一留在村里的高中生,平时喜欢高谈阔论,,但我坚信好多都是他编出来的。
“一个嘴上没毛的年轻人,倒像是你看着这些领导人长大似的。”有人说。
“诸葛坐南阳便知天下事,今年春灌是不是我舌战群儒咱村才排在第一浇的地?”锦程拍着胸脯问。
“尔呸……只说你过五关斩六将,却不说你喝多米汤尿那一炕……”胤山提着烟袋唱唱悠悠走来了,老蔚摇着蒲扇跟在他身后。
今天他们的大儿子建功回来了睡在瓜园里,他们才回了村。众人会出意后都哈哈大笑起来。胤山一来,故事就多了,他的肚子里装满了戏文,随便拿出来一抖,便是一地的故事,刘秀十二走南阳、珍珠粉碎白玉汤、诸葛祭灯、杨门女将,我有限的历史知识都是在这棵老槐树下听来的。
“唱一段,胤山叔。”
胤山慢悠悠地坐在青石上,磕了磕烟渣,清了嗓子:
“汉高祖当年把业创,
依仗韩信和张良,
登基后未央宫中斩韩信,
逼得张良归山岗,
汉刘秀中兴凭的是邓禹姚期马武将,
登基后也是杀忠良,
贬邓禹斩了姚家将,
逼马武碰死在午门上,
把这些能杀善战能掐会算的英雄好汉好比那雕梁画栋,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俱遭恶火丧;
思想起我杨家痛肝肠,
国王家的江山是臣创,
臣好比牛吃草来蚕吃桑,
老牛力尽刀尖死,
蚕丝吐尽在滚锅里亡,
这才是伴君如同羊伴虎,
忠臣好比草上霜……”
皇帝大多是昏君,即使创业时骁勇善战,文韬武略,守业时依然会变成糊涂虫,枉杀忠良。戏里的情节大都是这样,悠悠的苦音慢板在如水的月光下行走,夹杂着这声声叹,仿佛历史正穿透时空从大槐树的空腔里走来,我的脑子里出现了金戈铁马,征战沙场,生离死别,老泪纵横的画面,再转回头看时,暗影里,裂开的树身好似一本卷了边的书。
老蔚低着头归置蒿草,然后又点在四周熏蚊子,间或瞟一眼胤山,眼睛里满满都是笑意。
(三)
暑假的早晨常常从晌午开始,但今天我早早就醒了,是被吵醒的-----八婶家盖房子时挖出一副棺木。我跑去看时,已经围了一圈人,卡拉站在最前面,伸着脖子向下看。棺板已经朽了,八婶忍痛拿出自己结婚时的大木箱,把骨殖连同陪葬的毛笔铜钱一应儿搬进去。八婶一向细相,但这次却顾不了太多,只想请这一位早早挪了地方。庵里常住的那个老太太也被请了来,和四奶奶、十二姑婆一起焚香念经。骨殖到底被挪到哪里呢?又让大人们犯了难,除了家族祖坟就是责任田,祖坟当然不能进,也没有谁愿意在自家责任田里埋上一副不想干的骨殖,僵持到下午,这个描金的大木箱被放进村北山崖上一个废弃的洞里,全村人的心才都放下来了,但到底是祥与不祥,又开始议论纷纷。
大人们总是这么大惊小怪,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自从去年爸爸给我讲了鬼火便是磷火之后,我便再不相信有鬼,可要是当众说出我的观点,我妈总会呵斥我:“碎娃家的,别乱说。”
卡拉第二天下午就闯祸了。他和一群小子跑上山,爬进洞,把昨天安置好的描金箱子打开了,拿了里面的毛笔和铜钱玩,天快黑时,把箱子里的头骨像皮球一样踢下山,踢进村子里。
炸了锅了,这回炸得更大了,一群小脚老太太一边天塌了般地骂自己的孙子,一边心急火燎地去小卖部请了香烛纸裱。我奶奶去世早,婶婶提着鸡蛋去央告十二姑婆在黄裱纸上添上卡拉的名字,十二姑婆叹着气,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扫了一眼鸡蛋,然后在黄裱纸上歪歪扭扭写上一个奇怪的符号。我一直都在琢磨那个符号怎么就能代表卡拉的名字,突然想起来十二姑婆是不识字的。不识字的十二姑婆用一个奇怪的符号接通了人鬼两界,她用自己的旧围裙包着头骨,一边摇摇摆摆地走一边絮絮叨叨地念着经文,几个小脚老太太毕恭毕敬跟在后面大气也不敢出。头骨第二次被安顿好之后,泥水匠用土坯封了洞口。
写了名字的黄裱纸是一封致谦信,能用毛笔陪葬的必是一位知书识礼的古人,他或许能原谅这一群懵懂小童的顽皮,保佑他们顺顺利利长大成人。
我去婶婶家时,卡拉正站在墙根抠手指,眼睛红红的,脸也哭花了,怕我看出来艮着脖子不看我,我塞给他一颗糖,他噘嘴吊脸地推开了,我像个大人般叹了口气,点了点他的脑袋:“你踢的时候怎么不想你妈会打你!”
几天之后的庙会冲淡了所有人对这件事的关注,庙会是每年农历七月十二,我们都叫七月十二会,虽然只有三天,但是这个村子最盛大的节日。
空落落的一条街突然被从天而降的小商贩挤满了,卖凉粉的、卖豆腐脑的、卖醪糟煮麻花的、卖甘蔗的,每个小摊上都围着人,锣鼓锵钹紧火火地敲起来,大戏白天晚上连轴唱。家里突然来了七姑八姨,我妈一天三晌呆在厨房里做饭。
庙会最核心的会场要算北山上的庵里,从下午起便坐满了老太太,大脚的自己走上来,小脚的让人背上去,清一色蓝布衫黑扎脚裤,齐声念起经来嗡嗡嘤嘤,仿佛一层乌云低低压在头顶。我只上去过一次便不肯再去了,陪大姑走到山脚就坐在路边等她。
大姑是我们家最厉害的人,说起满清人的姑爸爸时,我常常想起我大姑。奶奶性格刚烈争强好胜,大姑完全秉承了奶奶的性格,七岁时就领着长工下地干活。爷爷懦弱老实,作为大掌柜的太爷爷就挑了奶奶做独生儿子的媳妇。大姑长大之后嫁给了附近财东家的儿子,那时已经不是因为门当户对而是因为成分相当,姑伯被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塑造成了类似爷爷的性格,大姑也像奶奶当年一样撑起了那个家。暑假一开始,我和卡拉有时就会跑去大姑家玩,有一次,大姑顶着烈日到河边摘回个大南瓜,有人问:“给侄子们做啥好吃的?”大姑笑吟吟地说:“看女”。
《看女》是秦腔里的一出戏,讲的是婆婆虐待儿媳偏袒闺女后被教育的故事。戏里的婆婆是个白脸尖嘴画着一颗痣的丑角,欢天喜地高潮迭起地挎着篮子去给闺女送南瓜包子,这一折戏笑料百出,在秦腔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大姑在闷热的厨房里蒸了一晌的南瓜包子,却不曾想小孩们最不喜欢吃南瓜,包子上桌时卡拉一口都不吃,我勉强吃了个包子皮,大姑哄了半天只好气哼哼地去擀面了。
黄昏总是惬意的,蚂蚱在脚下乱蹦,风从村庄的方向吹过来,一漾一漾,无遮无挡地掀起我的裙角。山脚是黄昏,山顶还有余辉晚照,九宗山脉宛如一条青龙在湛蓝的天边起起伏伏,唐王陵矗立在龙头的位置之上幽幽绽放着宝蓝色的光,它端正、雄浑、饱满、威严,像一位正襟危坐的长者,又像是爸爸写在图纸上的仿宋字。山陵的形态正好符合了我对李世民的想象,他是戏里唯一一个开创江山而后又明察秋毫的君王,视谏臣为镜,写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明白人。我们村叫胡都村,相传这里曾是庵堂下一片无边的荷塘,山上的庵堂原来也是几进几出雕梁画栋的大殿,只是后来破除迷信,姑子被遣,大殿做了爸爸小学的学堂,,大殿彻底被拆光了,只剩下路边那些断了头的石羊石马。如果没有七月十二的庙会的延续,这些大概都要被尽数忘光了,现在的庵堂早其实只是几间在当初的位置上由老婆婆们凑钱盖起来的几间茅草房子。
蚊子从草丛里出动了,嗡嗡嘤嘤在我身边乱舞,金龟子从卷曲的嫩叶里爬出来,摇摇晃晃继续向上攀登,青草飘着草香,野花散着花香,隐隐约约从庵堂的方向飘来诵经的声音,太阳彻底下山了。山上都是梯田浇不到水,所以大多种了红薯,红薯秧绿盈盈地爬成一片,盖住地面,就像爬墙虎,只是它们是顺着地面爬的。和庵堂一路之隔的,是我们家的祖坟,坟堆也是绿的,完完全全被带刺的荆条覆盖,那里埋着我的奶奶和爷爷,以及爷爷的爷爷,虽然后留下的坟头不多了,但就像是另一处宅院,故去的人都住在这里,大姑在庵堂里烧香的时候,我坐在这里,仔仔细细把他们都想了一遍。
第一天的新鲜劲一过,庙会就变得没多大意思了,大人们去看戏,我们拥在后台看演员化妆,期间有个演员,勒着头,白着一张脸,趿着鞋在后台走来走去,看见我们就拿着竹竿过来轰,那样的不可一世,不知道是个什么人物,等到一上台一看,原来只是个木头一般站在台角的兵,我们在一旁嗷嗷的喝倒彩,她再来轰,便没有人理她了。我不喜欢看这样的戏,胤山会讲戏,他们只会咿咿呀呀地唱,而我又没有耐心听。
庙会赶完了,就该上学了,大人们都说:“赶紧都关到笼笼里去,劳死个人咧。”我喜欢上学,卡拉就不一样了,他这会安静下来了,坐在石墩上出神地望着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报名的那一天,学校来了个照相的人,在墙根搭了布景,箱子里放着各式各样的道具。
我捧着塑料花,卡拉带着大盖帽,端着驳壳枪,我弯着眼睛,微微露出牙齿,尽量笑得漂亮些,卡拉抿着嘴唇,笑得有些腼腆,猛地变成梦寐以求的模样,他突然羞涩起来了。
赵维娜,女,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散文、小说多篇。
我在梦里想你,我在渭风等你
长按指纹>识别二维码>添加关注
投稿邮箱:2063526091@qq.com
主 编:成掌印
副主编:刘宏民 查改选